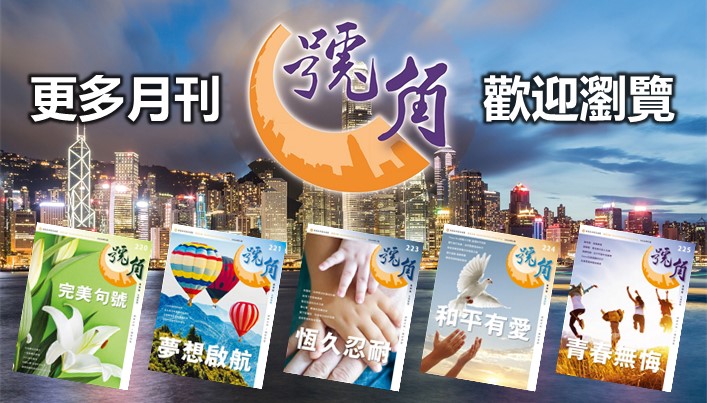日本長崎26人殉道記
自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於1547年來到日本九州傳教以後,在耶穌會的主導下,天主教在整個九州地區迅速發展。至1580年,僅耶穌會一個修會在日本即擁有15萬名信徒、200座教堂及85名傳教士。
不過,隨著跨國貿易與宗教勢力的糾紛激化,天主教徒與本地佛教、神道信仰者間摩擦頻繁,甚至發生「吉利支丹」逼迫寺廟,反遭報復的事件。

政權與宗教的碰撞
同一時期,豐臣秀吉正展開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他於1587年率領大軍統一九州後,發現當地天主教勢力雄厚,遂對葡萄牙人的勢力產生疑慮。同年,豐臣秀吉頒布「伴天連追放令」,將天主教定為邪教,並下令驅逐外國傳教士。不過,著眼於貿易的實際利益,該命令基本上並未被嚴格執行,許多教友仍暗中維持信仰。
直到1596年「聖菲利浦號事件」爆發,西班牙船員誇口傳教士是征服的前鋒,使得豐臣秀吉深感威脅,遂下令嚴禁基督教,並展開真正的大規模鎮壓。
1596年12月8日,豐臣秀吉再度頒布禁教令。京都奉行石田三成奉命逮捕方濟各會與耶穌會的傳教士及日本信徒共24人。這24人被帶到京都川通橋邊,削去左耳,並在城內遊街示眾。途中,另有兩名照顧耶穌會士的人被逮捕,加入殉教者行列,總計26人。
百姓眼中的囚徒
這二十六人走向刑場的過程,本身就是一條漫長的殉道之路。他們從京都出發,被押解徒步穿越近千里的風雪。衣衫襤褸的隊伍在嚴寒中蹣跚前行,耳垂與鼻尖被凍得烏黑。押解的士兵手持長矛,逼他們走完這段公開的羞辱與死亡預演。
然而,在京都街頭、在堺市的港口、在大阪的城門,甚至在漫長的東海道上,這些身披鐐銬的囚徒卻以異常的平靜面對沿途百姓的圍觀、驚懼與憐憫。他們口中吟誦的祈禱,如微弱的火種,悄悄點燃路邊一些陌生人心中的光。
他們由京都中京出發,沿途經過伏見、大阪、堺、兵庫、明石、姬路、岡山、廣島、岩國、下關、小倉、博多、唐津、武雄、伊万裡、時津、浦上,直至長崎的西阪,全程近一千公里。
行至長崎,最後的時刻來臨。在西阪的山坡上,26座十字架已經豎立,迎接他們的到來。 26有十字架,一字排開,面向大海,超過四千民眾圍觀。臨刑前,保祿・三木與夥伴仍高聲宣揚信仰,彼此互相鼓勵、唱詩、祈禱。


赴死之路
當士兵將眾人粗暴地拖向刑架時,人群中的啜泣再也無法抑制。一名少年在士兵的推撞中跌倒,隨即被拖起,胸前那小小的十字架再次跌落塵埃。一個士兵不耐煩地一腳踏上去,木片碎裂的聲音雖細微,卻刺耳入心。當少年被釘上十字架時,劇烈的痛苦使他全身痙攣,喉間溢出幼獸般的嗚咽。然而,當刀鋒最終揮落,年輕的生命戛然而止,頭顱滾落,鮮血如泉噴湧,滲入泥土,無聲地滋養了次年春天破土而出的第一株嫩芽。
刑場並未因死亡而立即歸於寂靜。殉教者的遺體被禁止收殮,曝曬於曠野,任風吹雨淋、鳥獸啄食,以此作為對後來者最嚴酷的警示。然而,信仰的種子一旦落地,便有了難以扼殺的生命力。那些暴露的遺骸、斑斑血跡,和在寒風中碎裂的十字架木片,竟被一些信徒含淚秘密收集,奉若至寶。他們的血,在泥土之下、人心深處,默默醞釀著日後更加堅韌的根系。
這26人,包括4位西班牙傳教士、1位墨西哥修士、1位葡萄牙修士,以及20位日本信徒(其中三人是未成年者)。他們象徵著勇敢、信念與對信仰的忠誠,也標誌著日本史上首次由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基督徒迫害,影響深遠。 1862年,教宗庇護九世將他們封列為聖人,每年2月5日定為紀念日。今天,長崎西阪擁有紀念館及雄偉的聖人雕像,見證這段悲壯與希望交織的歷史。


 鎮壓的開端
鎮壓的開端
這次鎮壓只是開始,開啟了日本長達兩百多年的「隱藏基督徒」時代,以及更殘酷的迫害,島原之亂。
26聖人紀念館靜靜隊列於長崎西阪山之上,肅穆如沉默的紀念碑。它沒有張揚的尖塔,也無鮮艷的彩繪玻璃;灰冷的混凝土與方正的線條,似乎刻意抹去所有浮誇的裝飾,只留下壓人心魄的樸素和肅然。
 在澳門的大三巴博物館中也有紀念26人殉道的事件
在澳門的大三巴博物館中也有紀念26人殉道的事件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可福音八章34節
文:旅遊博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