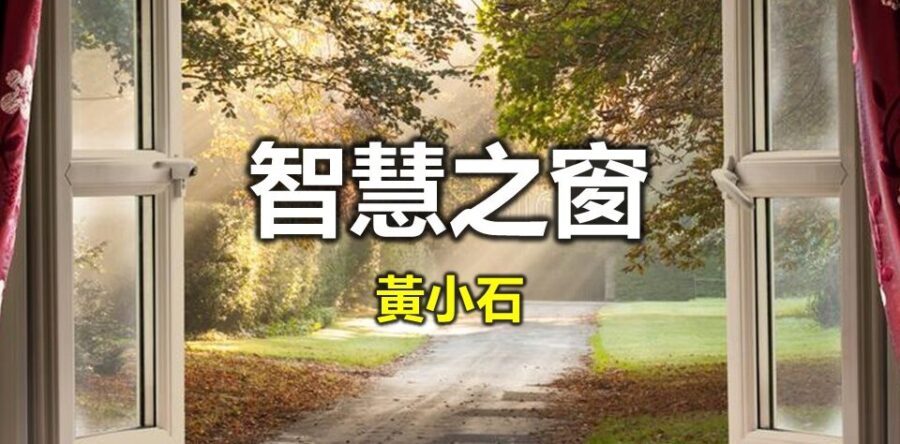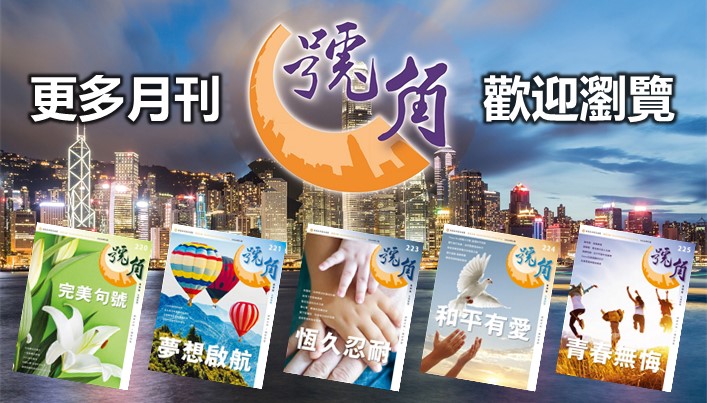真老
老人學家把老人家分成三類:65歲至74歲的人稱為「新舊」,75歲至84歲的人稱為「舊老」,而85歲以上的人則稱為「真老」。這三種老人是不一樣的,他們有不同的需要和特質,想想「老」的定義需要更正了。如今的「舊老」其實不算太老。近20年來,科學對人體的了解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從人體基因及一些病體DNA的解析中歸納出的全新醫藥及治療理念,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因為那個時代能活到80歲的人不多。連聖經都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
我忽然發覺自己已經85歲了,正是「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夢,不道消磨只數聲。」既然堂而皇之進入了「真老」之年,該有資格對「老」發表一些感想了:
(一)「舊老」不老
現在的「舊老」其實不算太老。有這樣的故事:「有位100歲的老人想要買人壽保險,保險公司不肯受理,因為他太老,風險太大。但是老人說他的媽媽有人壽保險,並且他媽媽已經120歲了,那麼為什麼他不能買保險?於是公司同意賣保險給他,並要他下星期二來簽字。可是他卻不能買保險?於是公司同意賣保險給他,並要他下星期二來簽字。說下星期二沒空,因為他需要參加他爺爺的婚禮。
當我踏入「新舊」之年的時候(75–84歲),除了讀書之外,又開始「聽書」,這不但省眼力,也可以在戶外邊走邊聽。因此我不惜重金購買了一副蘋果出產的「AirPods Max」,發現果然好用,且不會被風聲幹擾。近年來我每年可以讀/聽10本新書。俗語說得好:「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自忖本來學的就不多,不能再退了。
身體的功能也是一樣,需要刺激才能維持,因此我決定改變一些作息習慣。例如:4年前開始「間斷禁食」。先是採用所謂的16-8模式,基本上是從晚上8點鐘後不進食,直到隔天中午12點再開始進食。午餐是每天的主餐,晚上再稍微吃東西後就不再進食了。隔了兩年,我開始採用18-6模式,每天的第一頓飯在中午12點進食,傍晚6點以後就不再吃東西了。我維持這個習慣已經快三年多了,自覺精神不錯,體重、血壓、關節炎都控制得很好,尤其是後者,以前常有的風濕痛現在基本上都好了,並且晚上少吃,睡得也好。
(三)「舊老」更多多動
當我還是個「新舊」的時候,我努力每天走一萬步。進入「老舊」之後,決定每天多走幾步以便抵消老化,心想若不多動動就愈來愈不會動了。因此我刻意試著多走走。過去兩年每天平均走約15,000步,風雨無阻。當天氣實在太壞就去健身房的走步機走。一邊走一邊禱告或默想,或聽書,一天早晚各出去走一趟。我們住過的老人社區相當大,環境非常適合走步,不知不覺一小時就過去了。專家告訴我們,老人不但要多走,還要輕量舉重、游泳、打太極拳、做瑜珈等。我自覺沒有這麼多時間(和力氣),就選一項簡單的努力去做就好了。
(四)不去找病
再者,我看病的哲學是「我不去找病,讓病來找我」。我想沒病找病的人,遲早會變成「疑病症」者。我相信大部分的病是身體把自己醫好的。身體本是神奇妙的創造,詩人說:「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醫生許多時候只是幫助身體來「醫」好自己。中國古人說:「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這句話深得我心。只是我這個不去找病的「哲學」連妻子也不信。孩子中有兩個是醫學院的教授醫生,我也就知趣的沒有跟他們分享這個心得。當他們問我好不好的時候,我答:「蠻好」。 (學問就在這個「蠻」字上)
我的看病哲學不知道省了我多少時間(不是看病的時間,而是等醫生來看我病的時間),也省了不少錢。這不是我憑空建立的哲學,我從小被帶去看病的。古人說:「三折肱為良醫」,發現病大半是自己會好的。雖然說「藥醫不死病」,不過本來是「不死病」會不會給「醫死」了,卻是有些難講。近來有個報導,就是當美國洛杉磯郡的醫生罷工時,市民的死亡率不升反降。看來有些毛病不急急忙忙去找醫生,讓身體自己有機會恢復,可能是個老人可以考慮的選項。這可不是「醫學指南」,以上僅是個人經驗之談,連筆者的妻子及孩子們,都不同意。少讓病來找我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忌口」,中國人說「病從口入」這話是大有智慧的。
(五)「真老」是老了
進入「真老」之年,我發現短期記憶顯著變差,尤其是陌生人的名字,我聽完就忘了。為了要記得久一點(起碼在分手前還能記著),我總得問他的名字是怎麼寫的。因此當人告訴我他的名字是張三時,不免十分尷尬,但若不問一下怎麼寫,停一停,記一記,轉頭還是會忘記的。所以我的考慮是:「請問丁一先生,您的名字是怎麼寫的?」這樣雖然壞,但比起再隔一下又問他「您說您的名字是甚麼來的?」更壞!壞還是比更壞好。古人說:「千古艱難唯一死」,然而每個人都會死,看來似乎還不比學物理更「艱難」呢!活著的人既然都沒有死過,這不是一個實驗科學的議題,卻是一個最切身的議題。惟有那死而復活的基督才能告訴我們「死」是什麼。你也認識祂嗎?
文:黃小石(作者簡介)